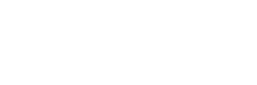羽田正说,他对“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产生怀疑,“是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多起由伊斯兰教徒制造的恐怖事件,以及此后日本和世界媒体铺天盖地的反伊斯兰教、反穆斯林的报道”的时候。
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日本学者。好像他们在大多数领域都能凭功夫做出骄人的成绩。最初接触到日本学者对穆斯林世界的研究,还是通过王柯先生论“东突”那本书的参考书目。逐渐了解到像佐口透、大石真一郎、山内昌之等这一领域中的优秀日本学者,通过网络或者图书馆检索到这些作者的作品之后,即使仅粗粗浏览,也会为他们的学问之精细和视野之开阔所折服。当然,这些人主要还是研究近现代历史的,更早一辈的日本学者中,对所谓西域史的研究,就更是人才辈出了。另外,现在比较流行的“新清史”,据说也是受到日本学者的直接影响。
最近读了日本著名伊斯兰史和全球史研究专家、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所著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一书。关于羽田正,之前上海书评已有过对他的访谈。他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祖父即著名历史学家羽田亨。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黄金期就是羽田亨与内藤湖南以及桑原骘藏一起造就的,他们为日本确立西域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内藤和桑原去世后,羽田亨率领宫崎市定和田村宝造将京大打造成了世界东洋史研究的据点。羽田亨的儿子羽田明是京都大学教授,他继承了其父在敦煌学方面的衣钵,是当代日本著名的中亚史学者,亨孙羽田亨一是西亚史(伊朗史)学者,另一孙子即本书作者羽田正教授。也许正是这个家学背景,使羽田正教授在此书中考察“伊斯兰世界”的概念时拥有特别宏大的历史视野,并能够对“世界”这一语素有较为全面准确的把握,在宏阔与精细之间拿捏得非常到位,细节的考订和理论的自觉结合得很巧妙。
本书与爱德华·萨义德的《报道伊斯兰》在取向和目的方面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萨义德主要从媒体层面梳理西方对伊斯兰的报道和研究,而羽田正遵循的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开辟的路径,并使之具体化。他力图从东方学家对“伊斯兰世界”概念的知识累进中揭示“东方主义”。
本书大体上共分为三部分,分别从近代以前穆斯林自身的世界观和世界史认识、近代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和发展以及“伊斯兰世界”概念在日本的受容和展开三个大方向上对“伊斯兰世界”这一主题展开论述,每一部分都有详尽的学术史梳理,并随时与绪论中其归纳的“伊斯兰世界”一词的四种含义(下文详述)对照结合,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在论述现代国际形势及国际政治之际……(原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所指)应该被单纯地命名为“多数穆斯林居住的地区”(194-195页);
二、解构了“伊斯兰世界”这个混沌不清的概念,抛弃了“伊斯兰世界”的框架并不能解决世界史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日本)现行的世界史认识及其叙述方法”(188页)。
作为一个概念,“伊斯兰世界”自然要有明确所指,而作者通过对日本相关研究者的三名代表——埃及经济史学家加藤博、政治学者小杉泰和宗教学者中田考的“伊斯兰世界”论进行梳理归纳后,得出“伊斯兰世界”一词至少包含以下四种意思:
一、理念意义上的穆斯林共同体;
二、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6月改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三、居民多数为穆斯林的地区;
四、统治者为穆斯林且按照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的地区(历史上的“伊斯兰世界”)。
其中第一点是超时代的理念型概念,二、三两点主要与现代相关,是现实中存在的空间,同时也是超时代的。这四种意思中,只有第二点能够清楚界定地理范围。第四点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有边界,但由于近代以前没有清晰划分国界,因此边缘部分的归属并不明确。而且现代不存在这样的空间。另外,第三点指代的空间范围相当模糊(绪论部分,10页)。很明显这个概念过于复杂,语焉不详,根据作者引用的各种该概念的用法,不难看出其用法也相当混乱模糊。在第一部分对近代以前穆斯林所著世界史与世界地理的梳理中,作者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把全世界分为‘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两部分……只属于部分阿拉伯穆斯林,而且他们均是比较早期的著者”(56页),这一时期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简单易懂,且有明确的地理空间,即穆斯林政治势力统治的领域。而其变得复杂和模糊,则“归功于”西方的东方学的发展。
根据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的阐述,“……东方仅仅是西方为了自身行动中的现实效用以及西方思想的进步而所作的一种建构。作为一个明确的对象的东方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东方仅仅是一本模式化了的书,西方人可以从中挑选各种各样的情节,并将之塑造成适合于西方时代的趋势”。东方世界在东方学家看来,正如萨义德引用的马克思的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一样,承认东方曾经的辉煌,是为了来证明今天欧洲的胜利,而且证明,为了让东方重现昔日的荣耀,必须由西方介入或殖民。那么东方是谁、东方有什么特点,完全是由东方学学者通过一系列对东方语言的分析、对东方艺术的研究、对东方历史的编写等努力将东方学科化、系统化,从而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里,由西方的东方学学者所规定的。今天这个复杂的“伊斯兰世界”概念也是如此。
正如羽田正在第二部分中所论证的那样,通过东方学的路径,西方树立了“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与“欧洲”这一具有正面属性且实现了近代各种价值的空间相对立,但却并没有赋予其明确的地理范围。而作为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反应或者是反抗,伊斯兰主义者接受了“伊斯兰世界”的概念,却赋予它正面属性,用以作为一种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反抗西方的近似于理念上的“乌玛”(Ummah)的意识形态。但无论赋予它的属性如何,其滥觞都源自十九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的发展,其中自然包括东方学对“伊斯兰世界”的貌似客观的知识,甚至是对伊斯兰世界通史的编纂。可以说,现代“伊斯兰世界”的概念同古代具有地理空间的伊斯兰世界完全是不可能产生关联的,前者是东方学的产物,是一种强加给曾经具有地理空间而现在早已不存在的古代伊斯兰帝国的一系列观念和定义,而吊诡的是,这一系列西方强加的标签又成了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自我认同的标准。
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东方学之界定远东、黄种人的标准上。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在关于奇迈可《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的书评(《上海书评》,2013年5月12日)中有这样一段针对性的评论:“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但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而囿于至二十世纪中叶左右东方学家创造的“伊斯兰世界”史的成就,“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世界’由于被填充了历史而变得具体实在”,“伊斯兰世界”这一概念不但为西方社会所接受,同样也为伊斯兰主义者所接受并不断固化。于是,无论是殖民时代,还是后殖民时代,双方的话语都是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的,不同的只是,西方代表伊斯兰讲话,抑或伊斯兰代表自己讲着西方人教给他们的话。
时至今日,这种含糊不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伊斯兰世界”概念,已经遇到了一个无论是西方还是第三或第四种意义上的伊斯兰世界(居民多数为穆斯林的地区和统治者为穆斯林且按照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的地区)都始料不及的现实,这就是伊斯兰国(IS)的建立。伊斯兰国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对其哈里发的效忠,在部分网站公布的地图上,不只是中东,从中国的新疆到非洲的马格里布地区,甚至包括印度在内都成为其目标领土(尽管图片来源真实情况待考证,但最近基地组织已经宣布加入伊斯兰国)。在笔者看来,这是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泛伊斯兰主义理念第一次获得相对成功的实践,他欲将羽田正界定的“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三、四含义强行统一起来,作为将来的目标。“伊斯兰国”的手段和理想是一回事儿,它的空间目标与西方语境下制造出来的含混的“伊斯兰世界”不无关系。因本文暂不涉及对IS的评价,所以不再详表。
羽田正虽然与萨义德遵循了同一个路径,但也有不同。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意义在于破而不在于立,通过对福柯知识-权力理论的借鉴,其目的在于使东方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惊醒。但醒来之后如何做?美国人类学家瓦里斯科在评价《东方学》时指出,萨义德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或许没能给出正确的答案。羽田正在《“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一书中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就此问题给出了一个坚定的解决方案:重写世界史!
通过本书对世界史著作和地理著作的梳理可知,近代以前的穆斯林知识界“并未对欧洲特殊看待,也没有生成‘伊斯兰世界’对欧洲的对比观念”(54页)。随着十八世纪末东方学的形成,“伊斯兰世界”的概念和“伊斯兰学”不断扩展,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第一部西方人(德·穆勒)编写的“伊斯兰世界”通史的出现,“使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世界’由于被填充了历史而变得具体实在……但二者意义不同,本来就不可能产生关联”(123页)。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东方学家创造的“伊斯兰世界史”已显露出明显的轮廓,同时伊斯兰主义者也开始主张书写自己的“伊斯兰世界史”。至此,双方的话语争夺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中展开拉锯,即在认可混淆了各种用法的“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框架成立的前提下,争夺一个对“伊斯兰世界”究竟是什么的表述权,却没有人怀疑也许“伊斯兰世界”这个框架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换句话说,如果“伊斯兰世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空间和过去实际存在的事实以及实在的地理范围相结合的概念是成立的,则必然会有“伊斯兰世界史”这一结果,反过来,如果这个“伊斯兰世界”的概念并没有明确所指,人们在使用的时候本身即处在语焉不详的状态,那么,基于这个概念下的“伊斯兰世界史”就是缺乏客观实在性的,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和错误的建构。
其实,根据作者考察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可知,“伊斯兰世界史”的框架与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史学教育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反倒是日本的史学基础教育中,基于本国历史和国家政治需求固化了这个由“回教圈”衍生出来的“伊斯兰世界”的概念,并通过国民基础教育深入每一个人,甚至是作者自己的知识背景中。但实际上,“以往被用于说明‘伊斯兰世界’特征的诸多要素,其实只是以‘伊斯兰世界’的存在为先验前提然后被附着于该世界上而已”(184页)。而现在,这种近代特有的历史认识和思考方式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作为一个东方学的产物,一个与“欧洲”对立而生的概念,欲打破“伊斯兰世界”的框架,就一定要同时打破“欧洲”的框架。作者认为,通过提倡“历史地区”的概念,即“在过去的某个时代设定一个地球,用地区研究首发来阐明其整体情况,在此基础上通过重合叠加这样的历史地区构成现代世界”的方法,加之对历史地区的人类和环境生态之间关联方式史的考虑,才能真正打破十九世纪以来一直存在至今的西方和伊斯兰的二元对立结构。
羽田正说,他对“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产生怀疑,“是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多起由伊斯兰教徒制造的恐怖事件,以及此后日本和世界媒体铺天盖地的反伊斯兰教、反穆斯林的报道”的时候。这与萨义德写作《东方学》时面临的黎巴嫩内战所引起的西方对中东的密切关注有着相似的背景,大概也因此,两者在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方面也是相似的。《尹文子·大道上》曰:“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也。”对“伊斯兰世界”的反思和建议是基于作者对日本学术史和国家政策的思考,也充分体现了羽田正作为一个全球史研究者的关怀,而这种反思、建议和关怀的意义早已跃出日本学术界了。■
本文作者董雨,文载2015年5月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