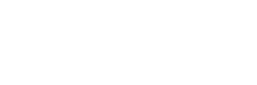2017年4月11日下午,我中心客座研究员、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杨文炯博士莅临我中心作报告,中心主任白贵教授主持了报告会,中心任文京、金强、邸敬存等研究员及硕博士生到场聆听了讲座。
杨文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结构的再认识——人类学的视阈》。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伴随中国的崛起,关注“中国”的“学术”话语成为热点,但如何理解中国在当今强劲的全球化语境中,对于中国学术界有着特别的意义。
杨教授认为,不论是西方传统的“东方学”,还是时兴的“新清史”,乃至从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到巴菲尔“新”发现的“危险的边疆”,乃至新近提出的亚洲内陆边疆的中国,重新解读“中国”都成为一种西方的学术“时尚”,而这种充满政治话语意蕴的“时尚”也也同样深刻地影响到了国内学术界。在国内学术界,不论是反思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乃至“去政治化”的争论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纷争以及何为“国学”的追问,这些话语都指向多民族的中国——深陷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水火不容”的学术话语的泥潭之中,成为了“如何理解中国”走不出的迷思。
杨教授进而指出,我们的学术困境就在于认知方式和话语桎梏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历史观。正如西方学者早已指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别的视角或思想风格”。(Guido Zernatto)正是这样一种“视角和思想风格”——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制约了我们对自身的多民族“中国”的理解,恰似“盲人摸象”或“郑人买履”。
杨教授认为,国内有学者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依附于西方的一些“时髦”理论而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尤其“建构论”所表述的“想象的共同体”给今人的历史错觉似乎是“中华民族”没有它的根性。这种被“规训”的学术话语不仅使我们自身的学术理性失语,而且自身变成了被自己遥远“凝视”(gazing)的“看客”,成为了西方民族主义历史观的一种镜鉴。
杨教授认为,从人类学的视角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推动力:一是内部的文化发明(即自我创造、创新);二是外部的文化借用(即文化传播或交流)。但凡人类史上能够在大浪淘沙的历史的长河中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文明无不合此二力而用之,中国文明亦如此。
讲座中,杨教授用大量的田野调查图片做了诠释,重点讲解了兰州灵明堂拱北和河湟民族走廊两个个案,用以解释多元族群和宗教文化可以达到融和汇通。杨教授进而认为,河湟民族走廊作为中国地理的几何中心和多元民族、宗教文化汇通融合的核心文化区又是观察、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最佳视点。
随后,到场学生就相关议题向杨教授提问,杨教授一一解答。最后白贵主任做总结和点评,白贵教授补充说明了从呼和浩特到新疆的另外一条驼队商路,以及连接内蒙与外蒙的丝绸之路,并认同“儒释道伊”共同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提法,各民族应该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时提出要以宽广的胸怀来看待人类文化,努力构建国内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进而将我们的经验带到全世界,促进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白贵主任做开场介绍

杨文炯教授作报告

报告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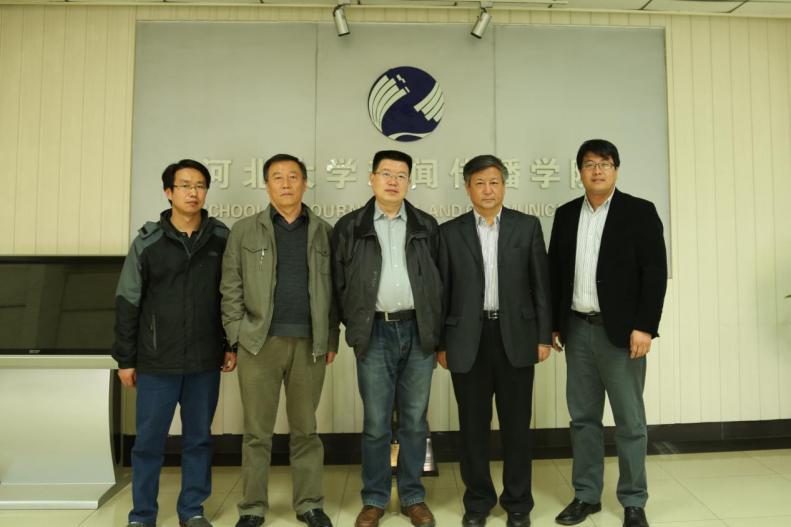
会后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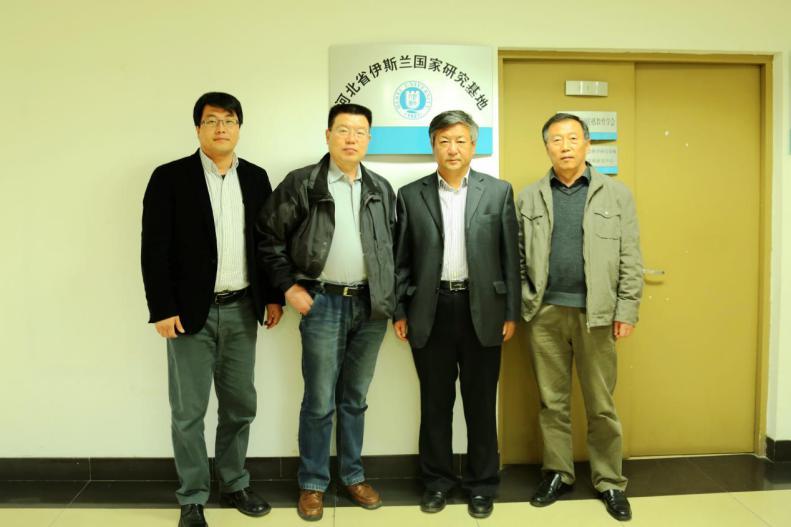
在中心办公室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