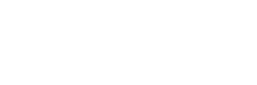载于《中国研究生》2015年第8期
持大学术视野,践行人文情怀
——访河北大学白贵教授

在学生眼里,他有着“歌唱家”的风采,紧跟潮流,是学生心目中的“男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师生的严格要求,使他“不怒自威”;熟悉美学、热爱艺术,厨艺纯熟,爱好广泛。他用企业家理念经营新闻学院,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优秀人才;以人文情怀和国际视野,执教四十载,桃李满天下。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白贵,即入耳顺之年,还在舍、得之间继续奉献能量,践行教育家的理想——教书育人!
从“文学才子”到“文艺青年”
记者:白院长,听说学生时代您就是很有名气的“才子”,在那个时代,您是所谓的“文艺青年”吗?
白院长:现在说的文艺青年跟那个年代不太一样,我们那个年代的文艺青年比较多,实际上还可以分得更细一点,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文学青年”。我们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学生,在77级中文系的学生里面,很少有因为没有合适的专业而选择中文系者,基本都是文学爱好者。虽然在进大学之前就发表过一些诗歌作品,我后来发现自己的才能不在诗歌方面,所以上大学以后,写诗就越来越少。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同学比我更有诗才,所以兴趣就慢慢转向文艺理论、美学,偏重于做学术的研究,大学期间呢,就发表过几篇文学论文,有的还被转载,引起学界关注。
那个时代的青年很多痴迷于文学,能够进入中文系,是一种荣耀。图书馆期刊室里所有的文学期刊都会被借阅一空,总有很多非中文系的、包括理工科学生也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杂志,——这种情况在后来就很难见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学生都热爱文学,甚至是迷恋文学,所有的文学杂志销量都非常好,一个普普通通的省级文学刊物销量达到几十万是司空见惯的。
记者:经历“文革”年代,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白院长:“文革”十年期间,大学没有通过高考招生,青年大部分被挡在大学门外,所以头一年恢复高考之后,报考的人数就很多,但是录取的又很少。“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以说是打破了“左”的桎梏,为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文学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引擎,揭露、控诉、反思“文革”,成为那个时期文学的一个主题,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学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一些著名的作品,如徐迟写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在那个时代,一个有影响的作品出现之后,全国人民都争先恐后地来阅读,每天早晨在各大图书馆开门之前,人们就排起长队。就像郭沫若先生在中国科学大会上所做的报告——《科学的春天》,其实不仅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文学的春天。
“文革”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我们都不愿意那样的年代再出现,但是历史既无法假设又难以更改,历史夺走了你一些东西,它同时又赋予了你一些东西。所以“文革”对于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历炼。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他们都是“50后”,我们同属一代人,他们的执政理念、能力在国际上受到好评,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历,经历过红卫兵时期的狂热,下过乡,受过磨难,后来又读了大学、研究生,是伴随中国社会的成长而成长,经过磨练,最熟悉中国的国情,而且从知识结构、社会阅历到心理素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可以说是历史造就的一代人。我们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也受到了磨砺。这种“丰富”是人们不愿意经历、避之不及的,但历史是无法选择的。客观上,苦难造就人,就像人们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年代、社会转型时期,会产生大量的题材,这有利于文学人才的成长。就像民国时期,特殊的年代成就了许多大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造就了一大批像“郭鲁矛,巴老曹”这样的作家,道理是一样的。
丰富经历只为教育初心
记者:从学生到老师,然后涉足职场----主持人、编辑、阅评员、广告策划,再到现在的院长、教授,您在每一步做选择时的考量是什么?是什么人或是力量推动您一直往前走?
白院长:在上大学之前,就当了中学语文老师,那时候我还不满二十岁。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考入大学,到现在已经工作四十年。年轻时就觉得当教师、培养人才很好,人才是所有的产品中最重要的产品,所以为国家培育人才是个很神圣的事儿!过去有句话说,教师是阳光下最好的职业,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出于对它的热爱,尽管那时候教师的待遇也不高,但我还是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大学毕业后也有从政的机会,但是我都放弃了,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一直走到今天。作为一名文科教师,我认为应该了解社会,了解跟自己专业相关的领域,所以我就在大学任教的同时,给出版社当特约编辑,为报纸和电视台做一些撰稿和策划的工作,给电台做兼职直播主持人(有三年之久),也包括给一些企业做策划,给新闻管理部门当阅评员,我觉得这些工作经历都对我大有助益,为我后来转型到新闻教育领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使自己深入地了解了社会,接触到社会中的不同人群。比如说主持电台的节目,嘉宾有省委书记这样的高层领导,也有普通人,主持人的身份可以让自己接触从社会高层到社会底层的各类人,这使我能很好地了解社会。不同的职业,优势和吸引力也不同,但从个人的性格和兴趣上来说,我还是觉得做一个老师好。
教育家品格,企业家意识
1981年河北大学建立新闻专业,是“文革”后全国第一批设立新闻学专业的院校。1995年成立新闻系,2000年成立新闻学院,那时候全国有新闻学院的学校屈指可数。1998年、2000年,河北大学分别获得新闻学、传播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5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新闻学专业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首批特色专业。2010年,学院获得新闻与传播硕士、出版硕士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3月,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为一级学科博士点。至今共培育了1万余名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生遍布中央、地方的各个媒体,有很多成为媒体的骨干和领导,还有一支活跃在教育战线的师资队伍,分布在海内外46所大学,继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新闻专业人才。
记者:您说过“办好教育还需要有某种企业家的眼光,把学院当作生产人才的企业来经营”,您的经营经验是什么?
白院长:教育跟企业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我们生产的是一种特殊产品——国家需要的合格、优秀的人才。对教育工作者而言,要有教育家的品格,不能只满足做一个教书匠。因为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发展。对一个学科的带头人和学院的当家人来说更是如此,不能只满足于给学生传授知识,把他们送出学校,有一个饭碗。我的想法是要输出优秀的、有后劲儿的人才,特别是有大爱、有理想、能担当、能包容、有能力、适应时代要求的专业人才,那么除了有教育家的品格,还要有企业家的意识。比如说企业家注重质量管理,企业家有竞争意识、品牌意识,企业家要拿产品说话,奉献最好的产品,有竞争力的产品,我们也是如此,要把这种意识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中,让每个老师明白,我们不光是要教书,我们更要育人。
记者:河北大学新闻学院要办成一流院校,看来必须先树立品牌意识。在您看来研究生培养,人文素养和跨学科视野十分重要。您作为创院院长院长已进入第16个年头,从十几年前媒体对您的的访谈中就看到,您一直强调人文素养和情怀,强调不要画地为牢,倡导跨学科学习,倡导跨文化交流,在这两方面,学院是如何加强的?
白院长:我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和想法,比如说,要让学生心系祖国还不够,我们要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再一个,就是不能满足于我们在大学里面获取的知识,因为知识是会不断更新,旧的知识会淘汰,一个“口袋式”的知识分子和毕业生,他在社会上是很难长久立足的。所以我们强调良好的品格,以胸怀天下为己任,要有一个很开阔的胸怀、善良之心,要有非常好的沟通能力--人际沟通、族际沟通、国际沟通,这样的沟通能力很必要。教师首先要有相应的意识,我们一再强调,要让教师扩大自己的视野,不能只盯着专业,一定要同时关注专业领域之外的东西;我们还有意识地在教师队伍当中力争多样互补,引进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进入到我们学院的教师队伍里来,这样对于学生来说,有助于实现知识结构的不断互补,对于教师来说,也有利于彼此之间的合作,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据说,您非常“惯着”自己的老师和学生,请来国内外各路“神仙”讲座,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和大量的讲座、交流活动,拓宽视野、增长见识,赢得校内外称赞,这出于怎样一种初衷?
白院长:我做很多事是追求从教育家的眼光出发,尽可能最大限度地给师生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成才环境。因为我们是一个地方性大学,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要调动、利用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我们的课堂要把所有的窗都打开,迎接八面来风,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吸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养分。当然,我们也鼓励学生走出去,去实践、去了解社会,去经风雨、见世面,这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为了培育人才。所以我邀请人来讲学,也不仅仅是讲专业的内容,专业以外的各个方面都要让大家有所了解,因为对于传媒人,很难说什么知识是不需要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担任院长15年,一直是这样做的,把我们现有的经费和资源用到极致。
记者:学院有来自很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从您的教育体验,也包括在跟国外大学交流和合作的经验中,您觉得中外的差异在哪?
白院长:走出去很重要,请进来也很重要。外国留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同时也会了解中国文化,这对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播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同时,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其他文化,因为世界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我们必须对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有全面的了解。走出去、请进来多了,国际化程度会自然地提高;国际化程度提高了,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每一个留学生,每一个外教都是一面大大小小的镜子,我们可以看到他人,同时也可以看到自己。相互学习、共同交流、共同提高。国内国外的研究生还是有差异的,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都是年轻人,都对新事物满怀兴趣;不同点就是因为外国研究生的文化环境不同、成长道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所以使得他们有不同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不同的精神追求,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客观存在。有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到较好的学术训练,比较规范。他们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似乎也比中国学生浓厚。
把握时代脉搏,心系天下
记者: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跨文化传播已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和研究领域。但是相比欧美,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似乎很大。在学习和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如何更好传播中国文化?
白院长:“一带一路”是中国一个全球化战略,这是中国走得很大的一步棋,它也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更加注重对外传播,国际交往,这是我们应该下力气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这里面也有历史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奋起直追,相信这种情况会很快得到改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讲现代人的概念,现代人要有现代意识,能够与人合作、要善于与人沟通。全球化时代,一个人如果孤陋寡闻、少见多怪,他必然是难当大任的。那么对于国际传播来讲,我们一方面希望别人了解自己,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别人,双方相互了解,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在对外传播,我觉得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每年新闻传播学的毕业生有很多,但是能够肩负起这个使命的人并不多,其中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很多人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只了解一些皮毛。所以很难系统地、深入地、全面地向国外的朋友们,向其他文化系统的人们来介绍和传播我们的文化。所以,首先是人的问题;再一个是传播的渠道、途径,传播的渠道和途径在不断地建立,进展还是不错;另外,就是传播的资源和传播的方法滞后,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能够赢得世界的尊敬,在文化上光有自信不行,必须有能力。如果光有自信,很可能自我陶醉、顾影自怜。如果我们有能力把我们的文化精华传播到国外,那么我相信,凭着中国文化的独有魅力,它会征服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记者:胡适先生说“敬慎无所苟”,要说自己能够负责任的话,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中,您也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怎么理解它的必要性?
白院长:做学术研究,规范和严谨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都是共同的要求。学术研究主张用充分的材料、证据来支撑你的观点和结论,我们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切忌没有多少材料发空洞的议论,做毫无依据的判断。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的生产是呈几何状在增加,我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而人的生命相对没有延长多少,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会面对大量的信息,尤其是碎片化的信息。碎片化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比我们的前辈接触到更大的信息量,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使我们难以专注,使我们的兴趣点不断地转移,使我们的知识建构呈现一种碎片化,我称之为“缀合效应”——我们的知识结构就像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一样,连缀而成的一个东西,它缺乏系统性、缺乏深入性。所以现代人的一个毛病就是不愿意深入思考,不愿意独立判断,喜欢受媒体的影响,容易受他人意见左右,这是一种时代病。我们要做出权衡,有取有舍,也是一种读书的艺术、学习的艺术——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是在手机上、网络上获取知识,信源单一,那就造成了一种局限,所以不能做“低头族”,获取信息应该是多渠道的。但是要记住,信息永远不等于知识本身,信息也不能代替思想,更不能代替智慧。
记者:互联网时代,处于媒体转型期,学界和业界都在努力寻求出路,似乎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该怎么面对?
白院长:简单地说,就是有变有不变。变,就是要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比如新技术。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手机解决,从获取信息到和别人沟通,从订购火车票、飞机票到转账、理财。如果你不掌握这些信息技术,那么手机对你来说就是单纯的电话。而对于能够应用它的人,手机就是一个多媒体,一个多功能的助手。今天,我们不能拒绝网络,拒绝手机,否则就是把自己隔绝于互联网时代,这是行不通的。特别是我们学传媒的学生,要紧跟新技术,这是要变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的观念,比如说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越来越重要,不能只是讲传统媒体如何做新闻,这些都是要做调整、要改变的。不变的是什么?就是做人,做人的原则——心系天下、善良、包容、求真、公正,这些美好的品格,这在全世界的学校都是共同的追求。时代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人性不变,社会需要的东西不会变,因为这个社会需要秩序,在法律之上我们还需要伦理。人文情怀、理想追求是不变的,做一个有担当、有理想,具有现代意识的,掌握现代科技的,能够推动时代发展的传媒人才。
耳顺之年的舍、得和奉献
跟很多老师一样,白贵教授有自己的性格、追求和爱好。对于学生眼里他“不怒自威”的形象,他表示,“做什么吆喝什么”,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应该谋划院长应该思考的事情。作为一名教师,要为人师表,做老师该做的事情,所以不是说要刻意塑造一个形象,而是在努力地实践着自己的信念和主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给人一些印象,至于大家的评判,顺其自然。付出得回报,耕种有收获;师生的认可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记者:除了学术、教育和管理能力,您被赞誉为“中国好声音”,在美学和宗教文化方面也造诣极高,您的兴趣广泛——音乐、厨艺、垂钓、旅游等,作为一个大忙人,您是怎么做到的?
白院长:爱好毕竟不是专业,也不必说一定要达到多高的境界,你只要喜欢,去做就好了。我是兴趣比较广泛,爱好比较多,现在有一些爱好逐渐疏远了,比如我喜欢垂钓,但是很费时间,就很少钓鱼了;还有一些,像旅游、划船、踏青,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得不压缩它的空间或者放弃。有些爱好是从小培养的,还有一些是被逼出来的,比如厨艺,父母上班,家里没人做饭,所以我就得从小学着给全家人做饭,养成了“童子功”。其实只要用心学,什么东西都不难;再一个就是你把它作为兴趣、爱好,它就不是负担,无论做多少件事情,跨入多少个领域,都不会感到疲倦,所谓乐此不彼,就是此意!厨艺也是一种创造,烹饪艺术,有创造的快感在里面。至于学术领域广泛涉猎,是因为哪个方面的知识都想多了解一些,使自己变得更为充实,这都是我所渴望的!
记者:执教四十年,即将步入甲子之年,在事业和生活上,您下一步的规划和重心是什么?
白院长: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明年就到耳顺之年了,人总是要不断地回头看一下自己走过的路,有时候要总结一下。走过的路是有得有失,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喜悦也有困惑,甚至是一些磨难,这都是人生当中的题中之意,也不奇怪,这里面有自己的选择,也有的是在被命运推着走。至于未来,按照学校的政策,我还可以工作到七十岁,所以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延伸我的教师角色,继续教书育人,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培育更多新闻传媒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