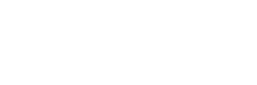摘要:尽管我们越来越强调周边外交,但有关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我们周边国家的研究,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说,长期以来都是非常薄弱的:我们既没有系统的学术积淀,也没有健全的学术梯队。
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学者,我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与战略的提出,对我们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地区国别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们智识的持续性的考验。
为什么这么说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我们很少有较为系统的关于周边国家研究的学术积累。这个原因并不难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视野主要地集中于西方、海洋文明(或曰蓝色文明)、发达国家的身上;所以,学英语、去美国留学一直是主流。体现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上,就是长期偏重于西学(且不论发展的质量,仅就数量来说,这个判断大致上是成立的)。尽管我们越来越强调周边外交,但有关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我们周边国家的研究,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说,长期以来都是非常薄弱的:我们既没有系统的学术积淀,也没有健全的学术梯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国内少有地保留着亚非拉研究中心(教研室/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单位,但在人才规模、体系化和招生等方面,仍然是捉襟见肘、面临诸多不足的。
在和几位从事中西交通或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前辈讨论“一带一路”战略时,他们都提到,放眼世界看看,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怎么可能不建立内陆欧亚研究方面的专业呢,怎么可能不去倾力打造和维系突厥学和伊斯兰研究的团队呢?为此笔者还去专门了解了一下:哈佛大学有阿尔泰与内亚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有中亚-高加索研究、乔治敦大学的中东研究世界一流,乔治·华盛顿大学数年前就开始打造中亚研究项目,印第安纳大学冷战期间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强的“内陆欧亚学系”,现在已经被提升并整合进国际研究的大规划,剑桥大学几年前已经将传统的东方学移到考古系并重组了中东-亚洲学院,就连哈萨克斯坦也刚筹建了突厥学研究院……
以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覆盖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传统区域研究范畴。回头看看我们国内的印度学、伊朗学、土耳其研究、俄罗斯研究,等等,除了个别地方偶尔会冒出朵奇葩来,基本上是乏善可陈的,尤其是苏联-俄罗斯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衰落。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人才的长期断档方面,近些年显得尤为突出。还是以北大历史系为例,在改革开放前培养的老先生们退休之后,竟然已经长期没有人教授和研究苏-俄历史了。就前述的所有这些区域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来看,目前的情况显然远远跟不上“一带一路”建设对我们提出的智识要求。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立足于区域和当地的战略,它的实践需要的是与各个不同的国家、文化和社区密切地打交道。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建设项目,不能只是建立在模型基础上的构思,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要“落地”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很多了解和懂得当地情况的人才,不只是语言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不只是学术研究的,更重要的是具有当地常识性知识的人才,尤其是有精力和活力的青年人才。
区域研究在国际上早已经出现一种分野,主要体现为传统区域研究与所谓科学的研究之间的分化。传统区域研究共享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古老传统,重视学习当地语言、当地联系和持续性的田野工作,当然,也强调与某一个学科(尤其是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的结合;新兴的区域研究侧重于(大)数据分析、建立模型,也就是所谓研究的科学性与量化,这一点对于传统区域研究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美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走向,也意味着传统区域研究的相对衰落(请注意,只是相对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统区域研究出成果比较难,人才培养也难,在经济情况不景气、教育经费相对匮乏的时候,从事传统区域研究往往更难;此外,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传统区域研究的成果转化也比较慢;而所谓科学的区域研究,就不太强调传统的那些严格训练,它训练的是另外的工具和方法,成材比较快,现在发表论文也比较容易。这是一个国际上的发展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区域研究行将消亡。科学方法的区域研究不能取代或取消传统的区域研究,传统的区域研究也不能排斥更先进的研究方法,两者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的。一位长期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俄裔英国学者曾跟我说,俄罗斯和中国在发展双边关系和区域战略方面,目前都面临着很大的智识上的不足,那就是,在俄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极少,在中国的俄国问题专家也极少,两国在很多地区问题上出现的失误主要一个原因是不了解当地国情。
第二个方面我讲一下“一带一路”给我们打开的新视野。我想追问的是:环绕着中国的海“路”和陆“带”,除了经贸方面的相关性以外,还与我们这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悠久历史、复杂族群和多元文化有什么有机的关系?当下的中国,一方面是综合国力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工资增长速度上也是最快的;另一方面是在国内外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尤其是来自内陆亚洲边疆的所谓“三股势力”的威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河殇》开出的药方是拥抱蓝色(海洋)文明,实际上就是“西化”,曾被批判为自我矮化、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带一路”是在中国日益紧密地融入同时也塑造着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如果说《河殇》时代人们对世界格局的认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那么,“一带一路”强调的“互联互通”则符合了中国一贯提倡的构建更为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美国一贯以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在非西方地区推行发展援助,其背后的逻辑和观念则是等级化的、是美国中心主义的,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发展主义的。“一带一路”强调的是互利互惠、平面化、网格化、多中心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
从中国自身的文明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说,“海上丝绸之路”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海-陆复合性特征,陆上向西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提出了反思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史观的时代课题。
一方面,中国既是海洋国家,又是大陆国家,大陆性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轨迹,“海洋性”没有得到充分认知。现代文明是海洋文明。“海上丝绸之路”逼问的是如何突破传统中国的海洋观。
另一方面,在历史观上,如何摆脱中原中心主义的陈旧叙事模式,客观地看到中国历史的内亚性和中原性的内在一致性,尤为重要。这不只是讲历史上的多次民族融合,也包括历史上出现的多个中国大地上的传统政权,都是中原性和内亚性的复合。
从这两个复合,即海洋与大陆,中原与内亚,可以清楚地为当代中国的定位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考路径,从而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持。对舒缓国内紧张的民族情绪,也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中国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人的身份和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流动不居的。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经常地就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我们处在绵绵不绝的时间洪流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个人或群体都要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总要不断地回到自身,重新地提出“我(们)是谁?”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是这样,对于长期纠结在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是这样,对于崛起中的中国也是这样。“一带一路”为我们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视野,说到底,也还是一个智识上的挑战与考验。
【本文原载《经济科学》杂志,是“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笔谈系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