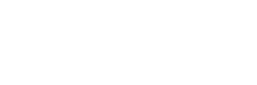美国学者本杰明·巴伯曾用“麦当劳世界”(McWorld)和“圣战世界”(Jihad World)来描述当今世界冰火两重天的状态:一边是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另一边则是反现代性和碎片化的世界。当下的中东为巴伯的理论提供了注脚。在动乱潮的冲击下,中东的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土崩瓦解。突兀而起的“伊斯兰国”像一块镶嵌在当代世界的“中世纪飞地”,屠杀斩首、买卖奴隶、毁坏文物,这些本应存在于历史书中的现象在这里大行其道。错愕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圣战世界”为何会出现,激进主义为何能把一些成长于“麦当劳世界”的青年变成嗜血的恐怖分子?
系 谱
“伊斯兰国”现象折射出的是一种宗教复古主义和激进主义,它是伊斯兰史上反复出现的复古运动的现代篇章。《古兰经》作为信徒心中的天启经典,“逊乃”作为穆斯林的道德楷模,萨拉菲(前三代穆斯林)时代被视为伊斯兰史上的黄金时代,从文本和历史两方面为复古主义提供了动力。但复古主义往往只在社会陷入危机时出现。历史上,伊斯兰世界曾引领风气之先,成为世界文明的灯塔。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和科技等方面都达到当时世界文明的巅峰。然而,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全方位地落后了。穆斯林救亡强国的复兴梦想屡受挫折,陷入了现代化的困顿和意识形态的混乱。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征服后,伊斯兰世界始终在探寻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是如何对待西方和现代性,特别是怎样对待现代西方政治的核心价值——世俗主义;二是如何对待传统,即本土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围绕这两个问题出现了三种思潮:第一种是全盘西化。伊斯兰世界堪称政治改革的试验田,源于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被逐一尝试。遗憾的是,它们没能帮助阿拉伯人民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最终都殊途同归,演变为威权或王权,没能超越“家天下”的藩篱。第二种是伊斯兰现代主义。主张先正本清源,重拾文化自信,然后学习并赶超西方。然而,方法论的错误决定了伊斯兰现代主义无法通过复古实现现代化,反而为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思潮提供了沃土。第三种便是宗教激进主义。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本主义相遭遇,产生试图通过回归宗教原旨,鼓动暴力反抗殖民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激进思想。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赋予了伊斯兰主义负面合法性。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替代品,获得运作空间和动员能力。同时,世俗政权对伊斯兰主义者采取高压政策,温和伊斯兰主义者参政之路被堵死,为激进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伊斯兰激进主义虽由现实政治所驱动,但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其源头可上溯至14世纪伊斯兰学者伊本·泰米叶的萨拉菲思想,历经近代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主义,再到当代埃及伊斯兰主义,一直发展到“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信奉的“圣战萨拉菲”思想。
伊本·泰米叶是萨拉菲派的奠基者,也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鼻祖。其思想的激进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定叛,即判定穆斯林叛教;二是圣战,即向悖信者和叛教统治者发动战争。他赋予了“圣战”前所未有的地位,认为它“比伊斯兰教功修中的礼拜和朝觐还要重要,比在圣地麦加居住更值得嘉许”。在一条教法律令中,他宣布向已皈依伊斯兰的蒙古统治者发动“圣战”合乎教法,因为他们虽口舌承认,但并未实行伊斯兰教法。
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内志地区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卜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他继承了伊本·泰米叶的思想,并更激进地阐释了萨拉菲思想的核心信条。瓦哈比派与沙特家族的结盟,推动了该派的兴起和传播,也为后来沙特阿拉伯的建国奠定了基础。
当代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源地则在埃及。在上世纪中后期纳赛尔政权的铁腕镇压下,宗教性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部分成员走向激进,其中穆兄会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的思想对伊斯兰主义的激进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库特卜深受欧洲左派革命思想影响,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宗教为外壳的现代暴力革命思想。库特卜思想的激进性体现在对国家与社会性质的二分法:一种是“人治”的“蒙昧时代”;另一种是实行“真主法度”的“伊斯兰国家”。据此,当下伊斯兰国家便失去了宗教合法性。他还强调穆斯林有义务反抗非伊斯兰政权,以恢复“真主主权”,隐含了暴力逻辑。受到库特卜影响,埃及伊斯兰主义者阿卜杜·萨拉姆·法拉吉将圣战提升为伊斯兰教第六项功修。
沙特阿拉伯是当代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另一策源地。得到沙特政治庇护的埃及、叙利亚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将伊斯兰主义与瓦哈比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反对王室的“新瓦哈比主义”。上世纪80年代阿富汗抗苏战场则成为吸引全球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磁场,为来自埃及和沙特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合流的契机,“库特卜主义”和“新瓦哈比主义”融合,形成了以复古和暴力为主基调的“圣战萨拉菲”主义。

信 条
“圣战萨拉菲”主义融合了中世纪萨拉菲思想、近现代萨拉菲—瓦哈比主义、当代伊斯兰主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该派思想中,“认主独一”是正统性基础,回归经训是阐释宗教的方法,定叛是批判现实的工具,“圣战”是达成目标的途径。它以严格的“认主独一”标榜自身正统性和优越性,自封为在“末日审判”时获得救赎的“获救派”,以末世论蛊惑人心;该派随意定叛,将当下社会和不遵从己派主张的穆斯林断为悖信者,占据宗教正统的高地,获得强大的批判武器;该派将事物分为“伊斯兰”与“非伊斯兰”,把人群分为穆斯林与悖信者,要求对穆斯林忠诚友爱,与异教徒划清界线;要求生活在“非伊斯兰疆域”的穆斯林,迁徙至“伊斯兰疆域”。
“圣战萨拉菲”的暴力思想主要来自对伊斯兰“圣战”观念的曲解,它将“圣战”提升为每个穆斯林均需履行的宗教功修,将政治反叛偷换为宗教战争,要求穆斯林对异教徒、穆斯林叛教者和非伊斯兰政权发动“圣战”。“圣战”、“为主道殉难”等观念被用于激进组织的行动动员,帮助暴恐分子克服恐惧,为暴力行为脱罪,并产生神圣感和预期回报,从而建构了“造反有理、恐怖无罪、杀人有功”的暴力逻辑。“圣战萨拉菲”还将“圣战”推向全球,从阿富汗战争起,“圣战”运动出现“游牧化”特点,“圣战者”在全球范围流动。从波黑和车臣,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哪里有穆斯林蒙受冤屈,大批“圣战者”便前往支援。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大同小异,前者萨拉菲—瓦哈比色彩较浓,后者有显著的“库特卜主义”烙印。受到古典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在伊拉克、叙利亚教派冲突的背景下,“伊斯兰国”对待什叶派等宗教少数派更加残暴。继承了埃及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基地”组织,则主张暂时忽略教派分歧,团结全体穆斯林对抗敌人。在建国问题上,“基地”组织主张“缓称王”,“伊斯兰国”则急于占山为王,建立“哈里发国家”。
实 质
伊斯兰激进主义利用宗教表达诉求,或以宗教的名义煽动暴力,但驱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某种具体的、真实存在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及其导致的怨恨。说到底,伊斯兰激进主义是一种反体系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国际关系理论家沃勒斯坦指出,伊斯兰主义是国际体系边缘地带挑战中心地带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其他激进革命思潮和运动并无本质区别。伊斯兰激进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两个范畴挑战现存体系的合法性:在国内,它否定世俗政权的宗教合法性,与官方伊斯兰争夺正统性,用激进的宗教信条动员群众;其国际议程则是颠覆民族国家体系,试图恢复用伊斯兰教法治理的“哈里发国家”和穆斯林“乌玛”。伊本·泰米叶用其思想反对蒙古统治者,瓦哈比主义则通过批判苏菲主义,挑战奥斯曼帝国统治。“基地”将矛头对准“远敌”美国,“伊斯兰国”则聚焦“近敌”,反抗伊拉克什叶派政权。
如今,反恐与去极端化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应对激进主义的正途应是消除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而不是与伊斯兰和穆斯林为敌。以“伊斯兰国”为例,该组织属于逊尼派叛乱武装,其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是伊拉克战争后,逊尼派被边缘化,美国不负责任地匆忙撤军,极端组织在萨达姆时期军官和逊尼派部落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壮大。
与激进主义的斗争是一场观念之战,在世界10多亿穆斯林中,激进主义者是极少数。伊斯兰教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中正、宽容、理性的资源,它们在抵御激进主义的斗争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应弘扬伊斯兰多元共存的精神。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信仰相同但文化各异的局面,这不仅使伊斯兰教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且可以成为抵御激进主义的宝贵资源。世界各地穆斯林应弘扬各自传统,彰显本土价值,赋予宗教以生命力和适应性,抵御一元主义的信仰观。教派共存是伊斯兰史上的常态,逊尼派、什叶派和苏菲派曾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长期和平共存。广大穆斯林应认识到宗教内部产生不同派别乃惯常之事,应以宽容之心待之。放大教派差异,随意定叛,不仅与伊斯兰正信相悖,还导致穆斯林内部的分裂。即使在逊尼派内部,四大教法学派也有差异。在伊斯兰史上,教法学家曾倡导在教法问题上求同存异,忽略细枝末节。
其次,倡导教法创制,使教法与社会现实紧密互动,与时俱进。主流宗教机构和学者若固步自封,在现实问题上失语,将给激进主义者曲解宗教提供空间。
第三,倡导理性主义。伊斯兰教将宗教知识分为传述知识和理性知识,前者指经训,后者指哲学、法学和史学等人类理性思维的成果。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内部对理性知识的贬低,导致文本主义和复古主义泛滥,使宗教思想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动力。穆斯林大众应当认清,伊斯兰激进主义属于“向后看”的历史主义,它沉湎于对伊斯兰黄金时代的追忆,企图通过恢复传统的方式建立一个“伊斯兰乌托邦”。作为一种反叛思想,它能破而不能立,绝不是伊斯兰世界发展和富强的药方。
从政治制度层面讲,阿拉伯国家均面临政治改革和转型的挑战,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需要恰当定位。宗教在阿拉伯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欧洲式的激进世俗主义在此行不通。伊拉克、叙利亚和突尼斯曾是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最彻底的几个国家,近几年却成为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最猖獗的地方。因此,阿拉伯国家需要探寻世俗主义的新内涵,找到一种符合本土价值和政治发展需求的现代性模式,在伊斯兰主义遭遇挫折后,探寻伊斯兰教在公共空间发挥作用,但不再坚持政教合一的“后伊斯兰主义”政治模式,充分吸纳现代性因素,才能建立适合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制度,为抵御激进主义提供制度环境。在这方面,埃及伊斯兰学者阿卜杜·瓦哈卜·迈斯里和突尼斯伊斯兰学者加努西提出的“部分世俗主义”和“程序世俗主义”的观念,均为解放思想、重构政教关系的有益探索,应当得到伊斯兰世界的重视。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10期,更多精彩内容请见《世界知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