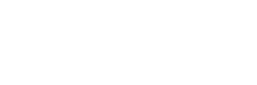【编者按】
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总部7日遭到武装人员袭击,12人丧生,震惊世界;9日,巴黎发生连环人质劫持案,四名人质在袭击中丧生。这一系列暴恐事件的意义之于法国,恐怕不亚于911之于美国。
反恐行动结束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对全国的讲话中指出,恐怖袭击的制造者只是“狂热分子“,恐怖袭击事件与宗教信仰无关,法国不应该因此被分裂。
曾几何时,在西方社会中,宗教越来越不重要一度成为一种“常识”,甚至善思之人认为自己应该不思考宗教问题。然而,曾漠视宗教的人们如今又再度恐惧于宗教的大规模复兴,并继而将暴力与恐怖主义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狂热。例如,极端的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甚至说:“在本应理智和正直的人中,只有宗教信仰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推动极度的疯狂。”
带有宗教背景的暴恐分子加深了人们对于宗教的偏见,而宗教偏见再度造就社会撕裂,生成仇恨与暴力的土壤。在暴恐事件之后,巴黎发生了针对清真寺的报复性袭击。尽管政治家们一再在暴恐事件后分割极端分子与宗教人群的关系,但针对某一特定宗教、甚至宗教这个概念的偏见依然在滋长。英国著名比较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指出:在如今的西方,“宗教生而暴力”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不证自明的意识形态。
凯伦·阿姆斯特朗年轻时曾进入天主教修道院成为修女﹐对于宗教生活有过切身体验。911事件以来,她活跃于公众媒体,以英国天主教徒身份成为一名专精于伊斯兰研究的学者。 2007年,阿姆斯特朗荣获英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奖﹐奖励她对英国社会的贡献——引导民众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代伊斯兰。
2014年,阿姆斯特朗出版了新著《流血之地:宗教和暴力史》(Fields of Blood: Religion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书中指出,在政教分离这一现代政治原则下,大众倾向于认为宗教是造就世界上血腥冲突的原因。然而回顾历史,政治与宗教分离的过程纠缠反复、充满冲突。事实上,暴力同样是世俗政治的法则,其原罪并不能被归咎于宗教。例如,芝加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自杀袭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或任何宗教都少有必然之联系”。在黎巴嫩20世纪80年代的38宗自杀性袭击中,27宗是由世俗主义者策动,只有3宗由基督徒、8宗由穆斯林犯下。
阿姆斯特朗认为,宗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特定时期人们组织生活的方式,绝不意味着某种极端价值。只是在外来入侵和内部压制所累积的压力下,世俗社会的不满情绪摇身一变成为宗教冲突。或许正如英国保守主义者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所说,宗教以这般可怕的扭曲的形式重返政治,跟它最初的出现,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是对无情世界的痛苦回应。
本文节译自阿姆斯特朗2014年为《卫报》专栏所撰写的文章《宗教暴力的迷思》(The myth of religious violence),通过回顾“政教分离”的形成历史,她意在向人们说明,如今是放下世俗主义者对于宗教的偏见,正视宗教在社会生活的基础性角色的时候了。
反恐行动结束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对全国的讲话中指出,恐怖袭击的制造者只是“狂热分子“,恐怖袭击事件与宗教信仰无关,法国不应该因此被分裂。
曾几何时,在西方社会中,宗教越来越不重要一度成为一种“常识”,甚至善思之人认为自己应该不思考宗教问题。然而,曾漠视宗教的人们如今又再度恐惧于宗教的大规模复兴,并继而将暴力与恐怖主义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狂热。例如,极端的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甚至说:“在本应理智和正直的人中,只有宗教信仰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推动极度的疯狂。”
带有宗教背景的暴恐分子加深了人们对于宗教的偏见,而宗教偏见再度造就社会撕裂,生成仇恨与暴力的土壤。在暴恐事件之后,巴黎发生了针对清真寺的报复性袭击。尽管政治家们一再在暴恐事件后分割极端分子与宗教人群的关系,但针对某一特定宗教、甚至宗教这个概念的偏见依然在滋长。英国著名比较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指出:在如今的西方,“宗教生而暴力”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不证自明的意识形态。
凯伦·阿姆斯特朗年轻时曾进入天主教修道院成为修女﹐对于宗教生活有过切身体验。911事件以来,她活跃于公众媒体,以英国天主教徒身份成为一名专精于伊斯兰研究的学者。 2007年,阿姆斯特朗荣获英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奖﹐奖励她对英国社会的贡献——引导民众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代伊斯兰。
2014年,阿姆斯特朗出版了新著《流血之地:宗教和暴力史》(Fields of Blood: Religion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书中指出,在政教分离这一现代政治原则下,大众倾向于认为宗教是造就世界上血腥冲突的原因。然而回顾历史,政治与宗教分离的过程纠缠反复、充满冲突。事实上,暴力同样是世俗政治的法则,其原罪并不能被归咎于宗教。例如,芝加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自杀袭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或任何宗教都少有必然之联系”。在黎巴嫩20世纪80年代的38宗自杀性袭击中,27宗是由世俗主义者策动,只有3宗由基督徒、8宗由穆斯林犯下。
阿姆斯特朗认为,宗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特定时期人们组织生活的方式,绝不意味着某种极端价值。只是在外来入侵和内部压制所累积的压力下,世俗社会的不满情绪摇身一变成为宗教冲突。或许正如英国保守主义者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所说,宗教以这般可怕的扭曲的形式重返政治,跟它最初的出现,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是对无情世界的痛苦回应。
本文节译自阿姆斯特朗2014年为《卫报》专栏所撰写的文章《宗教暴力的迷思》(The myth of religious violence),通过回顾“政教分离”的形成历史,她意在向人们说明,如今是放下世俗主义者对于宗教的偏见,正视宗教在社会生活的基础性角色的时候了。
ISIS武装分子那些志在毁灭叙利亚、伊拉克等经过殖民反抗建立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战争,其残酷性令人想起横扫罗马帝国的蛮族,抑或征服大半个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铁骑。
奥巴马和卡梅伦都做出了切割暴行与宗教的努力,试图让人们相信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无关,但愤怒的民众并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长久以来,经历了无数宗教战争的西方国家深信,宗教所释放的狂热偏执唯有通过建立政教分离的自由国家才能遏制。于是人们疑惑,为什么穆斯林们仍然继续着神权政治,而不以政教分离的方式去解决他们目前的问题?甚至人们认为,穆斯林未能进入现代社会,正是他们拘泥于食古不化的宗教。
事实上,宗教成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追求只是近代以来的观念,政教分离是一系列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独特结果,并不能简单认为这一原则可以在每一种文化下发展。世俗与宗教的两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宗教”这个词,在其他语言里往往是指一些更加模糊的、宏大的、概括性的东西。比如,阿拉伯语的“dīn”意指生命的整个过程,梵文的“达摩”则涵盖法律、政治、社会制度和信仰。希伯来《圣经》中没有“宗教”这一抽象概念,同样,《犹太法典》明确地认为人的全部生活都应被引领至神圣领域。《牛津古典词典》认为:“无论是希腊文还是拉丁文都无词对应英语的‘religion’ 和 ‘religious’。”唯一满足现代西方“宗教是纯粹的个人追求”这一概念的传统,最早也只能上溯到现代早期的基督教新教。
宗教暴力的迷思
早期宗教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耶稣的著名格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并不是在为政教分离辩护,而是在争取产品的分配权。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犹太人被“以色列的土地及其产品属于上帝,所以需要交给凯撒的只是少数”这一信念鼓舞,才爆发了反罗马起义。而《古兰经》认为,聚敛私人财产是错误的,为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美好的社会而分享个人财富是值得赞许的。
此外,战争和暴力是政治的特征,并不是没有了宗教便会天下太平。因为在现代之前,宗教并不是一个封闭领域,它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战争之中。十字军东征虽可看做是出于宗教热情,但更是有其政治意义:教皇乌尔班二世进攻穆斯林世界是为了建立欧洲的教皇君主制;西班牙在分裂战争之后,为了在奥斯曼帝国的压力下维护国内秩序,才设立了宗教裁判所。而发生在16、17世纪的欧洲宗教战争,是我们今日将暴力行为与宗教相联系的起源。一般认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理念冲突,导致了35%的中欧人口在战争中死亡。但这场宗教战争其实也是德国皇帝、其他欧洲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间的政治斗争。事实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反而常常能越过信仰,联手作战。例如,天主教的法国在与同样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作战时,就常常受到新教贵族的支持。但是,并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战争看做单纯的宗教之争,也不能将其简化为“单纯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国家是为了政治目的是“利用”宗教。战争中的宗教因素无法简单与社会因素相割裂,人们为不同的社会理想而发动战争,其中宗教和世俗的因素是混杂在一起的。
世俗国家的黎明
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个小国都为自己的领土宣示了主权,并在一支专业军队的支持下进行绝对君主的专制统治,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力平衡,缓解了欧洲长期以来的国际战争。在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中,教会开始走向从属地位。“世俗化”这个词在16世纪晚期诞生,它最初指“商品从教会财产转让为世俗财产”,“世俗化”这个词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它不过反映了欧洲新权力结构的生成。而这一发展造就了新的宗教理解——个人主义的新教。中世纪的天主教是需要通过集体生活获得宗教神圣体验的。而在马丁路德看来,基督徒是独自站在主面前的,他唯一可依赖的仅有圣经。由此路德认为应该建立绝对主义国家,其首要任务是通过强制约束罪恶——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与个人独立自由的愿望紧密相关。
路德的新教宗教观是现代世俗理想的基础,但世俗化政治不一定就意味着和平。在德国农民起义中,那些反抗德国贵族集权政策的农民被政府残忍地屠杀。路德对此坚持认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世俗的国家就无法存在。
17世纪末,天赋人权理论的主要提倡者洛克强调,政教分离对于创造和平社会“极其必要”。因此他坚持认为自由国家既不能容忍天主教徒,也不能容忍穆斯林。在这个时期,政教分离论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对于殖民地的看法,正如在当代,世俗化理论将穆斯林社会不能实现政教分离视为不可救药的过错。洛克认为,原住民没有生命、自由或财产权利,美洲的原住民首领对领地不具有合法权利。世俗主义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但教会是如此错综复杂地纠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结构中,这使得世俗秩序的建立只能依靠暴力。
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宗教和政治的分离过程更是充满暴力, 1789年国民制宪议会的首项举措,就是要没收所有教会财产来偿还国债。其后,大革命更是演变为平民和宗教人士之间的血腥战争,革命者刚刚摆脱了一个信仰,就又发明了另一个,他们的新上帝是自由、自然与法兰西民族。当拿破仑的军队在1807年侵入普鲁士,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同样呼吁他的同胞为祖国舍身忘死——这是崇高精神的伟大体现,是日耳曼民族神圣本性的集中展示。如果说信仰是时刻准备为之牺牲的东西,那么对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信仰取代了对神的信仰。为国捐躯万古流芳,但为宗教信仰牺牲就不一定了。
“进步”的代价
19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民族国家中的人民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实现了为了工业生产的组织动员。现代通信技术帮助政府形塑与传播“民族气质”、“国家精神”,并令国家政治前所未有的渗入到普罗大众的日常盛洪。即使他们与统治者讲不同的语言,但如今国民属于“国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把这种国家强制力的整合看成是一种进步。他认为,这对布列塔尼人来说无疑是有益的,“落后时代的半野蛮遗民”成为法国公民,自然好过“固步自封,抱守向隅之憾”。
现代民族国家使得平等、民主、人权、理性、政治自由等崇高的现代世俗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去,人民不再受等级、行业或宗教信仰的约束。政府需要充分开发所有的人力资源,于是欧洲新教徒、英美的天主教徒这样的“外人”,也被允许进入社会主流。然而这种宽容是表面的,19世纪后期,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担心民族精神过分强调民族渊源、文化和语言,将会使那些与国家基调不相吻合的族群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根据人性和文明的发展程度,优势群体会因此要求全部的社会权利,而弱势群体会被消灭或沦为奴役,置于一种依赖性地位。”正如他所预言的,少数族群将取代宗教异端成为新生民族国家所不满的对象。1807年,托马斯·杰斐逊对军队发出指示,美洲土著人是“落后的民族”,要么被“消灭”,要么被驱逐。次年,拿破仑颁布法令命令法国的犹太人取法国名字,并确保每个家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婚姻是与非犹太人举行的。随着民族情感成为最高价值,欧洲的反犹主义日渐兴盛,并于二战达到其顶峰。
在第三世界, 基要主义运动与残酷扩张的政教分离运动一直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世俗主义的进攻使得宗教作出暴力回击。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每一个基要主义运动的根源,皆在于对被湮灭的深刻恐惧。他们相信,自由主义或世俗主义的建立将会摧毁他们的生存方式。
作为一个开明的穆斯林领袖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于1918年创立了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共和国,他非常受西方的欢迎,但他同时体现出世俗民族主义的残酷一面。他痛恨伊斯兰教,取缔苏菲派教团,没收他们的财产,关闭穆斯林学校,废除哈里发制度,并继续开展奥斯曼帝国的种族清洗政策:为了控制商业阶层,他驱逐了占资产阶级90%人口的亚美尼亚人和讲希腊语的基督徒,一战期间,约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20世纪第一起种族灭绝案中被残忍屠杀。
基要主义的回击
基要主义的回击
世俗主义统治者,常常踌躇满志地要建设欧洲那样的现代化国家。1928年,伊朗国王礼萨·沙阿·巴列维颁布《着装法》:他的士兵们用刺刀扯下妇女的面纱,当街撕成碎片。1935年,警方奉命朝反对《着装法》,进行和平示威的人群开火,数百位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杀害。
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政变推翻并囚禁了曾承诺进行民主改革的伊斯兰救国阵线的领导人,以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也遭到了这些违宪的军事政变,但由于政变钳制了伊斯兰教政府,部分西方媒体反倒为此叫好。去年穆斯林兄弟会被赶下台时,西方大松了一口气,但取而代之的世俗化军事独裁,其滥用暴力的程度远超穆巴拉克政权。
政教分离是欧洲历史进程中自然发展出的适应性产物,它未必是普世的。现代性在不同的环境里,现代性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许多世俗主义思想家认为“宗教”天然就是好战、狭隘、非理性和残暴落后的,是和平、安宁、人文且自由的世俗国家的“他者”。他们不过是带着自己愚昧的宗教信条,再一次地重复那种,把殖民地人民看做毫无希望的“原始人”的殖民主义观点。
欧洲的世俗主义、以及其对宗教角色的理解,只是一个历史的例外。未能很好地认识这一点,已经引起一系列后果:借由强制力来推行政教分离,便会激起基要主义。历史表明,基要主义运动总是会在受到攻击后变得更加极端。这一错误已在整个中东结出恶果:当我们惊恐地看到ISIS所造就的暴行后,我们总该足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残酷暴力正是源于、至少部分源于西方态度轻蔑的政策。
原文地址: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sep/25/-sp-karen-armstrong-religious-violence-myth-secular